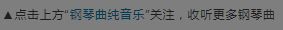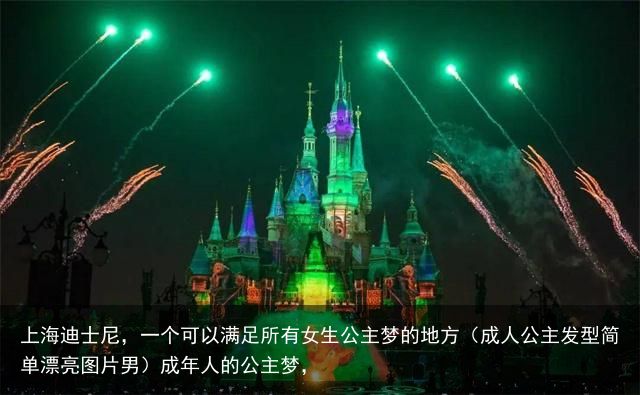青春如歌书声永|母校巨野一中记忆点滴(歌词中有我的梦想)儿童歌曲我的梦想,
作者|黄体军
一
岁月是用来记忆的,也是用来忘却的。
写作多年,从未触及中学六年的生活,是潜意识中选择了忘却,还是等待找到一把钥匙以打开记忆深处的闸门?

二
“巨野一中”四个字总是与少小离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到县城读书,到一中读书,至今仍是全县乡下孩子的梦想。
40年前,我便是这芸芸少年中的一员。
我相信,从自己的村庄出发到县一中读书,是众多乡下学子人生的第一次重要出发,县一中也成了他们最初梦想的托举之地。
三
1980年巨野一中面向全县招收初一新生,当年秋天我成了一中历史上初中26级1班的一员。
但开学前一个小小的插曲,差点将我挡在一中门外——
直到开学前一周,父亲还未筹到我上学应交的学费,这笔数额不大的学费当时对我们家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于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但家里迟迟筹不到学费,让年少的我经常茫然四顾,夜里躺在床上做各种上不了学的梦。
直到有一天——大概离开学还有三天,父亲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告诉母亲,学费终于借齐了。
我至今仍记得他满脸雕刻般的皱纹浮现出的喜悦之色。
一块石头落地,我转身流下了眼泪。
四

考上县一中的应该都是各乡各村的学习尖子。
小学阶段,我在老家截河村小学学习一直第一。
记得有一次意外失手,考了个全班第二,惴惴不安地回到家,等待我的是父亲一张铁青的脸。
原来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哥哥回到家提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父亲,结果那个失意的儿童被父亲狠狠地剋了一顿,大意是“你肯定骄傲自满了……”
儿童无言以对,他自问骄傲自满了吗?
好像没有,只不过在做数学试卷时遇到了一只拦路虎——
他本可以放过一道暂时求解无果的难题,但他固执己见,非和它较真不可,结果把后面的题也耽误了。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无论何种考试,他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
五
截河村离县城五十多里地,由于村子不靠公路,所以上学需要步行六七里路,去金山店子搭城乡客车,到了县城,从汽车站再步行三四里地才能到一中。
那时的客车又旧又挤,很少有座,加上路况差,印象中它总是行驶在一条尘土飞扬、颠簸不平的路上。
所以每次乘车,我总是默默祈祷它早点到达。
偶尔有一次,一上车我即幸运地得到了座位,不知不觉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车子在黄昏中穿行,仍未到达县城。
我竟然产生了希望它永远开下去、永远不到站的念头。
在我的印象中,它成了一辆永远开往未来的车。
这是中学六年我唯一一次具有幸福体验的乘车经历。
六
1983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成为巨野一中历史上高中22级6班的一员。
学习成绩上,初中阶段我在班里一般排到八九名,很少出前十名,但也很少进入前三名;高中阶段在文科班经常考第一,很少出前三名。
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加上学习任务繁重,导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高二第二学期末到高三第一学期,我曾得过一次心肌炎,回家打了两个月的针。
这对我的学习成绩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严重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结果没有考取自己心仪的大学。
如今回想起来,中学六年应该是我生活最艰苦的时期。
六年之中,几乎没闻到过饭香——这句话概括了我对中学时光最深刻的记忆。
一个两毛九分钱的咸菜疙瘩,我曾吃了一个多月,吃得嗓子疼;
很少订菜,饭筐中白黄黑三种馒头窝头,最后同学们拿剩的黑窝头肯定有我的份;
生活费时常不足,经常为不能及时交纳学费而焦虑。
后来很多年我不愿回忆这段岁月,可能与“艰苦”二字有关吧。
但它也塑造了我性格中坚强和柔韧的一面,成为千金难买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七
我们的初中班主任肖玉英老师,语文课张玉芹老师,高中班主任戴春祥老师、张尊忍老师,以及很多任课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很好的人;初中、高中很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很好的人……
八
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后,我曾试图和每一位学生建立互动关系,甚至试图让班里最弱势的学生、最边缘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一道特殊温暖的目光,一份具有特殊指向性的关怀,因为我就曾经是这样的学生。
也许做得不太成功,但我确实做过努力。
中学六年,占据了我们少年时期的全部岁月,而少年时期是人生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期——它的开始是童年的结束,它的结束是青年的开始。
所以,对于曾在巨野一中读书的学子们来说,无论人生之路顺利还是坎坷,无论梦想的终点圆满还是残缺,巨野一中作为一个特殊地标,都是他们无法绕过的地方。
九
中学六年是认认真真学习的六年,是真真正正打基础的六年。
每天早晨琅朗的读书声,已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校园记忆。
书声连接梦想,梦想终将实现,正可谓“青春如歌书声永,少年有梦终将圆”。
2022年是巨野一中70华诞,谨以此文向母校致敬。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