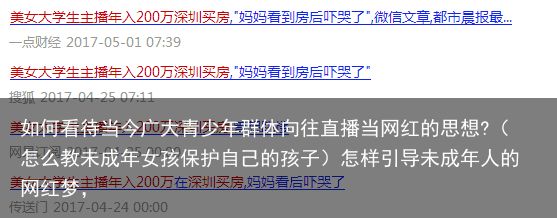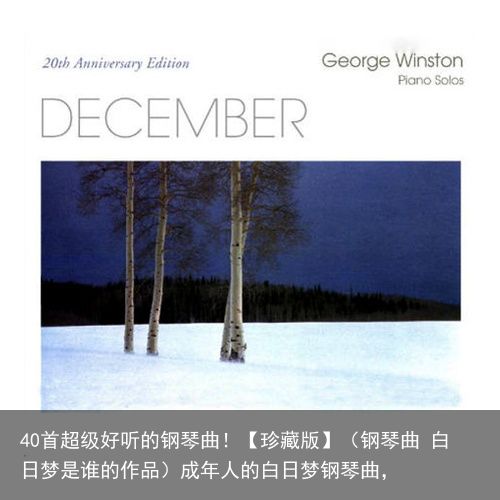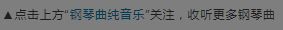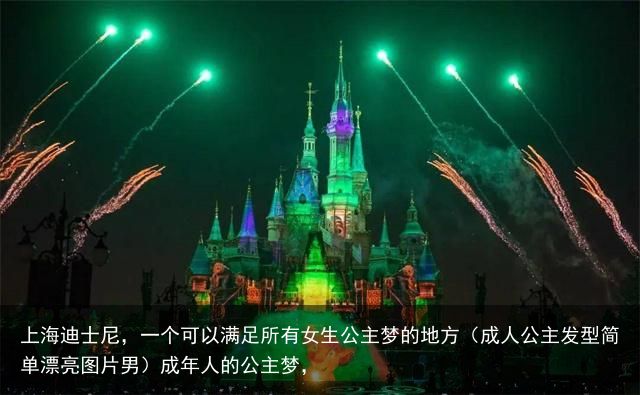他坚持二十年,用画记录自己的梦,还发展成了研究所(成人的梦想手抄报)成年人的绘画梦,
你常常做梦吗?一个又一个朦胧的,或者无比清晰的梦境。
李洋曾经是这样一个为梦所困扰的人。后来他拿起画笔。1992年,他第一次画下自己的梦:深夜,一个男孩行走着,手里提着一条大鱼的尾椎骨。
二十年后他对记者说:“梦既是创伤,也包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可以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档案。”
文章虽长,但值得一看。
 画家李洋
画家李洋
你常常做梦吗?一个又一个朦胧的,或者无比清晰的梦境。你可曾想过,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理想、一种困扰、未来的预言,还是,一种噪声?
李洋曾经是这样一个为梦所困扰的人。后来他拿起画笔。1992年,他第一次画下自己的梦:深夜,一个男孩行走着,手里提着一条大鱼的尾椎骨。画梦之旅,自此滥觞。
“梦既是创伤,也包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可以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档案。”二十多年以后,李洋对记者表示。

集体无意识:煤矿金猪,商品楼和大佛像,悲伤纪念碑
三十多年来目睹之怪现状,在夜晚以奇幻的蒙太奇拼接,不动声色地潜入李洋的梦境,这里面,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压制的,也有完全超出个人生活经验的。
李洋说:“我觉得每个人内在都是很丰富的,人都是朝着完整的人性去生长的,现代社会一不留神就会造就单向度的机器般的人,人的其他部分是被压制的,但在梦里,这些部分在拼命生长。”
 荒凉的煤矿里跑出一只金色的野猪,一只金色的野猪。它特别活跃,跳来跳去,在煤窑之上,那段时间煤矿老出事。
荒凉的煤矿里跑出一只金色的野猪,一只金色的野猪。它特别活跃,跳来跳去,在煤窑之上,那段时间煤矿老出事。 一个老富豪信佛。一天他豪掷千金把一带商品楼全部买下,之后把那片商品楼改造成一个壮观的大石窟,在里边雕大佛像。
一个老富豪信佛。一天他豪掷千金把一带商品楼全部买下,之后把那片商品楼改造成一个壮观的大石窟,在里边雕大佛像。 红色的教堂——其实是一个过去时代的纪念堂,是由许多老年人挥之不去的情感能量凝结而成的,所以老去的人们会去定期朝拜。
红色的教堂——其实是一个过去时代的纪念堂,是由许多老年人挥之不去的情感能量凝结而成的,所以老去的人们会去定期朝拜。 在洒满阳光的狭小套间里,李洋的周围一下子出现了数不清的水母样透明物体。它们一收一缩地,在空中缓缓浮游,若隐若现,飘忽无定。
在洒满阳光的狭小套间里,李洋的周围一下子出现了数不清的水母样透明物体。它们一收一缩地,在空中缓缓浮游,若隐若现,飘忽无定。对于上述最后一个梦境,李洋认为,这种悬浮透明生物的存在,显然与他所生存的帝都北京特定的物质现象有关——雾霾。并且,经由梦行使的夸张功能,这种长期存在的雾霾正演化出种种生物性。
通过长年累月对梦的记述,李洋慢慢感觉到,梦有重头大戏,亦有小打小闹。他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手段,去“强化那些正面大梦的能量,攘除负面梦的破坏性能量”,也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指的“积极想象”——以梦为起点,通过内容丰满的潜意识沟通手段,将一些内心压抑的情结和情绪抒发出来。
于是便有了李洋混合着梦境与现象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悲伤纪念碑》。故事里,人类制造了一种可以吸收大家悲伤的新型材料,建筑了一座“哭墙”——那些无处倾诉的人,像是被拆迁的、上访没希望的人们会去“哭墙”诉说哀伤。后来有人坐不住了:怎么能有这样的东西呢?把它炸掉!就炸掉了。但没人想到,这种材料具有生物活性,它会自己生长,慢慢长成一个巨人。跟着人们发现,那些拿着长枪短炮试图再次炸毁它的士兵们也会被它的悲伤感染,变得特别悲伤。大家对这种挥之不去的古怪生物感到十分恐惧,但束手无策。直到最后,人们后来发现这样的悲伤根本是无害的,而且中国需要这么一个释放悲伤的途径。
“我以前想,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是不是体制造成的,或者跟政治有很大关系?后来看了些身心灵的书,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会有些共同的心理上的东西,压抑、恐惧、茫然,美国也有,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把去看心理医生当作耻辱,别人比我们更正视这些问题。”

“拿一根大头针,把梦做成标本”
很多年里,做梦带给少年李洋矛盾重重:
第一,父母和学校期待他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而多梦让他变得细腻、敏感,有时还犯迷糊;第二,中医有种说法是多梦乃病态,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病”;第三,他始终困惑,这些梦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曾经刻苦想改掉这个“毛病”,举哑铃、长跑、拼命投篮,可是没用,夜里梦仍是一群等待破解的谜题,簇拥着找他。
李洋从小爱做梦。梦中仙鹤、神猴、大山大海,纤毫毕现。

不仅多梦,他还总能记住这些清晰的梦,甚至常常知道自己在做梦——按荷兰心理学家Frederik Van Eeden在1913年提出的概念,人在做梦时保持清醒的状态,这是“清明梦”。但在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首的欧美国家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梦境的种种解析尚未抵达前,1970年代,在主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山西太原一个铁路职工家庭里,李洋背着爱做梦的包袱,心事重重地长大。

适逢初中,为了锻炼作文能力以应付中高考,老师布置了写日记的家庭作业。李洋随手把梦当了习作素材,比如奶奶家朝东的窗外,“一对紫色大鸟,静静地停驻在槐树枝子上,保持着完全静止的姿态”,又比如半夜醒来,“一只身披黑灰色颓然乱羽的少年小鸡,直愣愣走过爸妈与我盖着的大棉被”。灵感源源不绝,还因此得到初中老师的赞赏。李洋感觉舒服多了,记梦便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此二十多年后,截至2015年,李洋记录自己的梦境4000多个,整理200万字,绘画800幅左右。
在这些梦境的日记最终发展成为李洋的个人史料之前,曾数度面临被焚毁的命运——工作和家庭都期待他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而心里堆砌的幻觉、情绪和前世今生,多少让他的人生显得虚无缥缈。
可是,“那些心里的一切,烧的掉吗?”
“梦和烦恼,像是蝴蝶或蟑螂,失控的时候,它到处乱跑,但当你拿一根大头针,把它做成标本,它就被你认识了。”李洋对记者表示。此时,中年李洋的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一名副教授,办过一些梦境的画展、创设了一个“梦研所”,正式把记梦这个秘而不宣的童年癖好,发展为自己成年后的主业。
他开始“老老实实面对自己心里的一切”,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踏实与靠谱”。
“红书”
而这些日复一日、庞杂纷繁的梦,如何阐释“心里的一切”?
面对这种伴随睡眠的生理过程产生的神秘心理现象,世界各地民间说法纷纭,但科学实证派多少有些回避。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派,则是前所未有地重视梦境,将释梦作为研究人心灵和精神病理现象的重要手段。

在网络上,输入“解梦”的关键词,各种流派各种理论扑面而来。原本李洋把梦以每夜为单位割裂开,单个单个地求解。但若干次求解梦受骗上当后,他观察到“释梦市场一个问题就是,抓住某个具体的梦拼命解读,而并不顾及它与你之前,之后做过的很多梦形成的序列关系。”他认为,真正严谨的释梦,需要长时间(例如三个月以上)记录并整理一个人的梦,待到大部分重要的梦主题有所基本呈现后,再做整体研究。这便是释梦的更高层次——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层次。
北京望京区,一间商业楼盘里的公寓。这里是李洋的“梦研所”里档案部的一隅,30个日记本将李洋童年至今的梦以编年史的形式呈现着。居于最高位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红书》——这位“双重人格”的心理学家,一度因备受幻觉折磨而濒于崩溃,而当他面临“中年危机”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活以探究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时,他以这部书记载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幻觉。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也曾在《红书》的标领之下,大张旗鼓地反思人类的梦幻和内在世界。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个体潜意识,你太关心自己了,你跟世界没有关系,有压抑,有情结,有创伤;荣格认为梦的很大部分跟人类整体的神话、传说,原始的共同记忆有关,所谓的原型记忆。”李洋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人的梦境有三个层次:
个体无意识层次,包含着对于个人生活的回顾、分析、整合、预言、提醒与总结。
集体无意识层次,包含着整个人类集体记忆的潜意识种子,常常与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时风议题有关。
通灵层次。

为了说明大部分人的梦还是跟生活、记忆、意境和情感有关,李洋把17岁时所作的200多个梦并置、分类,“中间那部分关于原生家庭和社区,左边那个关于大自然,右边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山、树、原野,男人和女人,城市和道路,物体……

这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梦境,往往从家蔓延开去,到奶奶家-姥姥家-母亲单位-父亲单位-火车站-小学-中学,地理上越来越远。
“大多数都会做关于家乡的梦,想是春运时上千万迁徙的人,都指向对家乡的一份情怀。通过这些梦直接就能反映很多跟经济有关的问题,比如城乡差别、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问题,而那些反映人们心理的问题更需要我们面对。”李洋对记者表示。

“小清新救世”
画梦的时间长了,李洋发现一条规律:
对于他画梦一事,五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包括父母)普遍不怎么接受,他们希望他去画一些“美好的”题材……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些人慢慢开始接受了。但在艺术圈内,到了80后、90后,他们热情程度超乎想象。
2011年,李洋把自己的作品《我在中国做梦》系列在豆瓣网上推出,几乎每个梦画下面都有很多人跟帖,聊自己的梦。开始有年轻人留言,想要李洋帮他们画梦。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天知道人们已经做过多少匪夷所思,却又和时代密切相连的梦了。如果有人系统研究、收集、整理、分析这些梦,不知道能够帮助多少人疗愈忧愁,发挥创造,产生连结,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纠正。”李洋想。
2014年4月,集合一些学生和艺术家,李洋成立了一个“我为中国人画梦”小组,并成立“梦研所”。下设档案部、理论部、妄想部、显化部四个研究与创作实践部门,外加一个教育部门:云中美术学院。
李洋从各个领域征集的梦境,现在已有第一批样本。

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憋毕业论文的时候,常常梦见自己被架在高处,怎么也下不来。类似的梦李洋也多次出现。也许地面上被害女子是个人感情创伤和欲望压抑的象征。

一对情侣的女方找到了李洋说,「他家人想要本地的女孩子,而我不是。我大三,过一个月要毕业了,也许真的很怕他会离开。」后来她做梦就梦见生病,她在输液,男的陪着她,照顾得特别好,手机突然就响了,传出一个声音说:你赶紧离开他,回家找个本地女孩子,然后男孩举着手机一步一步就离开了。李洋画下手机响的一瞬间,他们的手还是握在一起的。画完以后,女孩告诉李洋,他们又在一起了。
在梦里,这个女生总是在毗邻学校的一条长满青草、开满血色红梅的石板路上奔跑,躲避未知男子的追逐。 「内心的恐惧应该是六岁那年跑进去的。当时我从外婆家回到自己的家,因为不肯上幼儿园天天被打,每一次我都死拽着路边的青草不肯走,这也许是后来梦里反覆出现青草的原因。」女孩认为青草和石棉板是她隐藏内心恐惧的道具,而未知男子也许是她内心恐惧的象征。她对画梦的艺术家刘爽说:「谢谢为我画梦,对我来说做梦只是拂开内心表层灰尘的那只手。
在李洋搜集的样本里,弗洛伊德的性动力学说似乎是行不通的。李洋认为「跟性有关的梦只占几个,10%,或者更多一些,但不是全部,」这幅在10%之列,由艺术家刘洋绘制。女孩梦见和一个长着男人头的蛇在接吻,“可能当天见了自己喜欢的人。”她这样解释。
比较少有的幸福之梦,它属于一个小女孩,她在睡梦中笑得咯咯咯,睡醒伸个懒腰,梦见和一群小朋友在河边玩水枪。这个母亲对李洋说,“把这个梦交给你,是因为这个年月太缺少单纯的快乐了。”张慧绘制
这些绘本风的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这样主打严肃艺术的学院派里,并不一定算“高大上”。
“当代艺术有点瞧不上小清新,我恰恰觉得,小清新是特别救世的,卡通、手作、手账、羊毛毡、多肉植物之类,一个人倾心于这种东西,一定不会太贪,不会太功利。”李洋进而阐发道,“我特别好奇一个贪官会不会做梦?他的梦会鼓励他去贪更多的东西,还是让他良心不安呢?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忽略虚的东西了,才会在实的世界里拼命地抓。其实贪官是由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造就的,他的背后是有创伤的。”李洋相信,画梦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关怀,是对现实的关照,是治愈在社会发展中受到创伤的人们的一种方式。
由于人手和精力紧缺,“我为中国人画梦”的系列刚开了个头,还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
尽管过盛的梦境曾是李洋创作的源泉,但现在,“我其实是希望自己能不做梦了。”李洋说。他想有更多清醒的时间,把“梦”落到实处。
原文来自「开端文化」
跟大粤君一起,在广东发现有意思的人 ↓
| 他们都在这里等你 |
回复关键词就能遇见
汤唯:看了汤唯的孕照快爱不起来了,听完她的粤语回血一万点
木匠:他辞去世界500强主管做个木匠,喜欢的事也能开辟新世界
董明珠:董明珠和PAPI酱的关联,开启下一波财富源泉?
粗口:广东人爆粗全国最威?黄霑说他才不是香港粗口冠军……
宠物:有温度or痴线?宠物入殓师送它们最后一程
装修:花20万装修租来的房子 他说房子可以租生活不苟且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